从归途中寻找救赎之道
——评《追风筝的人》
刘苇
《追风筝的人》(The Kite Runner)是一部令人惊叹的小说。它在主题与人性上所涉及到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展现而出的丰富的地域与时代背景,使小说具有了非同寻常的品质。而这一切却是通过一种清澈、单纯的叙事来完成的。沉重主题与叙事上的清纯——这种“背反”的特质构成了小说特殊的魅力。犹如作者在轻声哼唱,你以为他在哼唱小调,其实他在吟唱交响诗的某个篇章。而其中,作者真挚的情怀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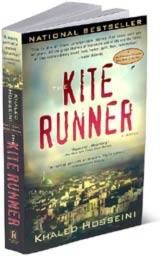 作者在真诚的语调下讲述了一个壮美而又凄楚的故事:一个逃亡到美国的阿富汗人在二十年之后又冒险重返战乱的阿富汗,目的只是为了自我拯救。因为作者的真诚,这样的故事遂使我们信服。我们认同作者的叙述,知道这样的事在现实生活中一再发生;并非只有小说里才有。而作为小说特性之一的虚构,在此,被我们认可为作者用来丰富小说主题的手段。作者的真诚,其实关乎一个重要的命题:赎罪。试想一下,如果作者缺乏真诚,那么小说中的赎罪主题,就会显得苍白无力或矫揉造作,小说也就不会具有如此扣人心弦的力量。
作者在真诚的语调下讲述了一个壮美而又凄楚的故事:一个逃亡到美国的阿富汗人在二十年之后又冒险重返战乱的阿富汗,目的只是为了自我拯救。因为作者的真诚,这样的故事遂使我们信服。我们认同作者的叙述,知道这样的事在现实生活中一再发生;并非只有小说里才有。而作为小说特性之一的虚构,在此,被我们认可为作者用来丰富小说主题的手段。作者的真诚,其实关乎一个重要的命题:赎罪。试想一下,如果作者缺乏真诚,那么小说中的赎罪主题,就会显得苍白无力或矫揉造作,小说也就不会具有如此扣人心弦的力量。
甚至,我更认为,小说作者在冒似通俗的故事里安放下这样一个重大主题的做法是特意为之,这在后现代阅读环境里是可以理解的一种做法,也是较为聪敏的做法。
小说通过两个副部主题:“信任与背叛”、“父子间爱与冲突”,逐渐延伸进“赎罪与救赎”的主部主题核心。两个副部主题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宛如大树下盘根错节的根茎,支撑着主部主题。在“信任与背叛”中,既有哈桑对“我”的信任与“我”对他的背叛,又有“我”对父亲的信任与父亲对“我”的欺骗;在“父子间爱与冲突”中,既有因“我”的懦弱天性遭父亲鄙视与为赢得父亲的爱而挣扎一生,也有父亲与哈桑之间隐形的父子关系而形成的爱与痛苦。最终,所有矛盾都汇聚到“我”身上。一个自身的迷宫与钥匙。
少年时代,哈桑因“我”而遭受街头恶少的围攻毒打,“我”却躲在暗处不敢出头,而后又胆怯地逃开。从此“我”愧对哈桑。为消除内心的耻辱,“我”使计诬陷了哈桑,从而使父亲被迫驱逐了他,并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但哈桑的离去并未消除“我”内心的悔恨与羞辱,反而像被蛇紧紧噬咬一样痛苦不堪。
小说主人公的错误不在于表面上的面对恐惧时表现出来的怯弱。恐惧感是真实的。而在于不敢正视自己的懦弱,并为了掩饰懦弱而进行的欺骗。这是一种双重的怯懦。这不是一个看似简单的良心问题。他驱赶哈桑,其实是因为害怕个人尊严受到损害。他以为只要赶走哈桑,就可不必面对羞辱,尊严得以保存。显然,他想错了。生活决不会轻易地袒护这样虚伪懦弱的人。
然而奇妙的是,不是出于某种外在的力量,正是出于他的内在的骄傲,才使他最终不能原谅自己。他陷落了悖论之中:只要他想维护尊严,就永远不能对自己的错视而不见。他绕不过去,也躲避不了。无论他远在美国,还是哈桑已经去世,他总要面临一个原先一直回避的问题:如何诚实地面对自己。一开始,他诋毁哈桑、欺骗父亲是想要自欺欺人,但他最后明白,谁都可以欺骗,就是欺骗不了自己。他原先希望借助父亲和婚姻的力量,以及时间(流逝的岁月)和空间(远离了阿富汗)上的距离来消除心中的罪恶感。但是,这种“他救”的方式显然起不了实际作用。一切救助只有通过自我拯救才能赢得彻底的解放。危难与解脱是同一个针眼,只有穿过它,直面危机,内心才能最终得以解除束缚。可喜的是,小说主人公最后正是这样做的。
还有一点易被人忽视:他内心萦绕不去的罪孽感,乃是出于他仍葆有高贵天性的缘故;因而也就有了自我救赎的可能。一个恶徒是不会产生像他那样的罪孽感的,也不会理解困扰他一生不安的原因所在。于是,主人公在阔别了二十多年后重新回到已是满目疮痍的被塔利班所控制的苦难深重的家乡,直面那个盘绕在心中的日久越紧的“蛇结”。如同在刀锋上行走一般,只有以死向生地去面对魔难的考验,才有可能获得救赎之道。
 阿富汗裔的美国作家卡勒德·胡赛尼(Khaled Hosseini),一定是在自己的童年经历过这样的事或从流亡的同胞中听到过类似事件的发生,并深深地触动他,才会使小说具有如此真实力量和震撼效果。小说还从侧面触及到战乱的阿富汗,从苏联入侵到军阀混战到塔利班残暴行径,它表明了一个个体,在剧烈动荡的社会面前显得如此弱小,宛如飘零的树叶,或被风吹向远方,或零落成泥。小说的尾声似乎蕴涵着一个显而易见的隐喻:此刻阿富汗依然遭受着战争的蹂躏,它的苦难远没有结束。《追风筝的人》所涉及到的主题沉重而发人深省。借用索尔·贝娄在别处所说的话,“他的小说简直就是从人生中撕下来的”。最后,我不得不引述伊莎贝拉·阿连德(我是如此赞同她)的观点,作为我对此书看法的一个概括:“文学与生活中所有重要主题,都交织着在这部惊世之作里:爱、恐惧、愧疚、赎罪……”
阿富汗裔的美国作家卡勒德·胡赛尼(Khaled Hosseini),一定是在自己的童年经历过这样的事或从流亡的同胞中听到过类似事件的发生,并深深地触动他,才会使小说具有如此真实力量和震撼效果。小说还从侧面触及到战乱的阿富汗,从苏联入侵到军阀混战到塔利班残暴行径,它表明了一个个体,在剧烈动荡的社会面前显得如此弱小,宛如飘零的树叶,或被风吹向远方,或零落成泥。小说的尾声似乎蕴涵着一个显而易见的隐喻:此刻阿富汗依然遭受着战争的蹂躏,它的苦难远没有结束。《追风筝的人》所涉及到的主题沉重而发人深省。借用索尔·贝娄在别处所说的话,“他的小说简直就是从人生中撕下来的”。最后,我不得不引述伊莎贝拉·阿连德(我是如此赞同她)的观点,作为我对此书看法的一个概括:“文学与生活中所有重要主题,都交织着在这部惊世之作里:爱、恐惧、愧疚、赎罪……”
(原刊《外滩画报》06年6月第三周)
版权所有 游吟时代 保留全部权利 © 2003-2013 Youyin.com